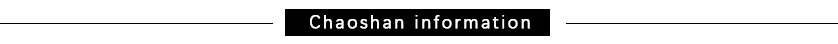
▼
 |
|
吴子野先生是潮州前八贤中最神秘也是最有趣的人物。他既无科名,也无当官,又无诗文集传世,却长久地享誉着“八贤”的盛名。
他少年喜任侠,像豪侠剧孟(西汉游侠)一样,气盖闾里,乐于助人,晚年则“不喜不忧,不刚不柔,不惰不修”,如同闲云野鹤云游四方。
他遍交公卿、名士知己。公卿如李师中、曾公亮、黄裳、解宾王、蒋之奇等;名士如二苏、苏门六学士、郑侠、钱世雄、曹子方等;诗僧如释道潜、释惠洪等;道士如蓝乔、李士宁、蹇拱辰、黄洞、何得顺、祖堂、通老等。他的朋友圈不分地位、不分年龄、不分学历。“虽无刎颈交,却有忘机友。”更可贵的是,他对朋友都“一无所求”。
他不管朝廷的“党争”,不管朋友是处于庙堂高位,还是成为“元祐党人”被贬于江湖,不管贫贱富贵,他依然故我,始终与之“相守到白头”。
他善于养生,却鄙视炼丹服药,九十多高龄还能渡海到儋州(海南)陪伴老友。
吴子野是何许人,老朋友苏东坡说:“吴复古子野,吾不知其何人也。徒见其出入人间,若有求者,而不见其所求。不喜不忧,不刚不柔,不惰不修,吾不知其何人也。”他是什么人,“从来非佛亦非仙”。
我一直想解开这位“清风万古,有道之士”的人生“文明密码”,探求这位可敬可亲的长寿老人的“人格魅力”,每每苦于文献稀缺,不敢“操觚以率尔”。
说说为何敢“操觚”。按某名人的说法,写文叙事要谈来龙去脉。那就先说“来龙”。
记得2003年,到广州开会,初识吴兄庆东,交谈,知他是揭阳炮台南潮村人。我半开玩笑地说,先祖是“吾邑之光”,潮州前八贤之一吴子野先生,了不起。之后,“吴子野”把我们拉近了。回到揭阳,不时相问讯。我好事,借吴子野“白云深处是吾家”诗句,再捡唐释皎然“闲鹤天边俱得性”为上比,凑成一联书赠庆东兄,以记因缘。
我素来喜静不喜动,有闲喜欢静坐乱翻书或涂涂抹抹。庆东兄以为这样不利于健康,某周末,驱车来,强拉我到郊外闲游,说是散散心呼吸新鲜空气。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也好。偷懒,“抄”拙文:
山野间树木蓊翳,绿叶红花枯枝藤萝,相互顾盼,又各不相让,“野芳发而幽香,佳木秀而繁阴”。树杪不知名小鸟,黑白相间,成群结伴,“鸣声上下,游人去而禽鸟乐也”。路旁杂草放肆丛生,竹下陡坡,有山野小花怒放于乱草丛中,花穿蓬蓬杂叶而出,娇小可爱,“嫩紫娇黄媚绝伦,一生山野不知名”,可嗅阵阵花香,书生眼中,颇多诗意。时阴雨过后,远处白云偶锁峰腰,露其顶如浮岛,尤婉约绝妙也。二三十分钟后,雾渐薄,峰峦由近而远,次第呈露,远山显出,天色蔚蓝,青翠清朗,倍有情致。山上松树虽非极古,高亦三二丈,长风吹来,拂松而有声。小道之下,为双坑水库,一片清秀,时闻水声潺潺。余等或疾步小道,视山面而行;或彳亍看花,以景色而停。
这样,每于周末风雨无阻,一行就是几年,自觉身心都不错。期间,庆东兄多次约到南潮村走一走,不知为什么,总是阴差阳错没有机会。一直到去年的某一日,终于到南潮村。闲步南潮村,谒吴氏宗祠,拜吴公子野,看百年古树,游揭阳古八景之一“双溪明月”,套用一句被人用滑了的成语是“大吃一惊”。“吃惊”,是因为揭阳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水乡,村里还保存这么多的古树。听村领导说村容村貌的近、远期规划。我觉得,如果打造得好,不比外省那些供人旅游的水乡差。更重要的是,这里还有一位宋代长寿名人吴子野。在南潮村,四处都弥漫着“吴子野”的絮语,散荡着淡淡的历史气息。归来后,写了一副联语以记南潮村之行,联曰:
百年古树绕堤绿,双溪明月春光好;
千载先贤传世香,二字和安秋水长。
所谓“和安”二字,是吴子野养生的宗旨,“复古安、和之对,得养生之术”(明林大钦语)。
干脆,再寻踪先贤的足迹,某日又抽空到潮阳金沟村麻田山拜谒吴公墓。金沟村也是吴公的后人。看看新“复古桥”和旧“复古桥碑”,新桥旁有一条六米长的老石板,据说是当年“复古桥”的桥面,粗犷浑厚而斑驳,静静地躺在古榕树下,卧听数百年来的风声雨声。再看看高大的“吴远游神道碑”,虽被多次迁徙,满身沧桑,如今仍屹立在路旁大树下,不卑不亢地注视着人来人往。这是进入麻田山吴公墓的序曲。
麻田山海拔二百多米,沿着山道拾级而上,“岭入金沟径愈幽”,路边泉水潺潺,泉涧上面都布满了杂草树枝,只闻水声而不见水,有名副其实的“听泉石”。“泉当蟹眼清如淀”已不见矣。方志说山上“有远游庵,宋高士吴复古栖隐处,〔吴〕先卜居于此,因葬焉”。明隆庆《潮阳县志》有较详细记载:
“远游庵,宋逸士吴复古栖隐处也,在直浦都金沟岭之麻田山中,前后高山罗列,中有岩石水泉之胜。其上又有来老岩者,亦为宋僧来逻禅定之所。咸淳中尝创麻田长生院于此,时有五色雀见,其上下有巨木,有白石龟,有渡人桥,又有亭在半山,翼然于紫翠之间,皆佳致也。今庵与院俱废,惟水石如旧。”
吴公墓是二十年前重修,我和吴公的后人毕恭毕敬地向高士鞠躬致意。墓的前沿杂草中深埋着一些石柱础和石龟,经过若干百年的风风雨雨,很苍老但仍稳健,像迷茫的历史皱纹,显然是昔年建筑物遗留的石部件,应是当年远游庵的遗存。望着这布满青苔、深埋于乱草丛中的石柱础,也算聊慰思古之幽情。咏苏轼“鸡唱山椒晓,钟鸣霜外声”,仿佛回到千年前吴公在麻田山的景况。只是千年沧桑,惟水石如旧,“古道馀残碣,秋山满薜萝”,然而“空山人去已千秋”。
潮汕宋代先贤多数没有著作留下来,以八贤中的七位宋人为例:许申有《许申集》,今已佚;林巽有《礼乐书》《草范》《草范先生文集》等,也佚;卢侗的《周易训释》,刘允的《刘厚中集》,张夔的《禄隐集》,王大宝的《周易证义》《王尚书遗文》也都已散失,他们遗存的仅仅是几首零星的诗文。这就使后人未能从文本上深入地了解他们,造成研究缺少主动话语权。数年前文友周兄修东撰《宋潮州七贤年谱丛刊》,我为之写序,既为他的辛劳予以致意,也说过很无奈的话:
“宋代潮人的著作流传下来的甚少。他们的治政思想、哲学思想等等,偶有一鳞半爪散见于各种资料中;至多,我们只能在别人零星而抽象的评语,来转述对谱主的某些苍白的判定而已,总无法直通谱主的思想脉搏,因而不能把他们具象化丰富起来。这致命的缺憾使研究者失去主动话语权,亦因此,研究工作的进展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。《七贤年谱》荜路蓝缕,功不可没。但愿日后能有更多宋代潮人的资料出现,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潮人有更上一层楼的了解。”
数年前,我之所以敢撰写宋《孙莘老先生年谱长编》,是因谱主的奏稿多数传下来,又有《孙氏春秋经解》传世,再搜集散见于各集中的诗文尚能编成《寄老庵存稿》一书。加上谱主和苏东坡、王安石等是同僚、文友,有不少唱和。这样考其行事,叙其仕途,录其诗文,谈其友情,算是有“料”。孙莘老(1028~1090,名觉,累官御史中丞、龙图阁大学士)的交游如苏东坡兄弟、苏门六君子、郑侠等等,也都与吴子野是好友,当日阅读宋人诗文集,顺便留心有关吴子野的资料,并录存于箧笥中。和南潮的吴姓朋友谈多了,他们要我写一点先贤吴公的事,我迟迟未敢贸然答应。原因是觉得吴子野的行事所知太少,又没有诗文传世。当再次细读宋人诗文集及一些方志后,想试一试。提起笔,即碰到如何写的问题。如果写《吴子野先生传》,嫌其行事太少。吴子野的简传在各种方志中,只存下几根粗线条的速写,如同不那么准确的国画大写意。这样的“传记”太苍白。
乱读闲书,见明代文士袁宏道《与徐汉明》信,他把知识分子活法分为四类:玩世,出世,谐世和适世。玩世和出世,则“上下几千载,数人而已”,难学。谐世,儒家积极用世的态度,袁中郎视为“措大”。适世,既不玩世,更不出世,也不用世,也与媚俗无关,是不道不儒不禅,“以为禅也,戒行不足;以为儒,口不道尧、舜、周、孔之学,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,于业不擅一能,于世不堪一务,最天下不紧要人”。他以为这样才能葆有纯真的人性,葆有生活的乐趣。袁中郎对这种活法,说“自适之极,心窃慕之”。
大喜,吴子野先生不正是这样葆有纯真人性,葆有生活乐趣的人吗?这样的生活境界不是很令人神往吗?他就像宋代汝窑天青纹器皿一样,简洁朴素,没有一点火气,却很温厚很有韵味。应该写,值得写。就写他怎样“适世”,怎样遍交公卿、名士知己而一无所求。于是,郑重决定向龚自珍的写诗法学习——剑走偏锋。
我把吴子野的友人分散在各种集子的言论积攒起来,从中勾勒出吴子野的侧影,进而解读这位千年前有点神秘的、葆有纯真人性的长寿老人,使他的风范略微展示出来。
写到这里,我仿佛看到这位一千年前的“适世”老人,捋着银白的长须,从揭阳南潮村出发,迈着健步,又要四方云游了。是要到潮阳麻田山中卧听天籁“绝粒不睡”,还是要到潮州城内岁寒堂品赏北海十二石,或者是要到外地晤二苏谈诗文论养生?也许,是要找蓝乔、蹇拱辰、陆惟忠诸道士探讨“不死五通仙”吧。真如张文潜所说:“我亦有心游八极,从公一借葛陂龙。”这都成为文化的呢喃和暖暖的记忆。
|
你是本文的第626位读者
来 源: 摘自“汕头日报”2015、10、18
作 者: 孙淑彦
|
| |
| |
| |
▼

特别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《图·文》来源于国际互联网,仅供参考,不代表本站立场!
本站尊重知识产权,版权归原创所有,本站资讯除非注明原创,否则均为转载或出自网络整理,如发现内容涉及言论、版权问题时,烦请与我们联系,微信号:863274087,我们会及时做删除处理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