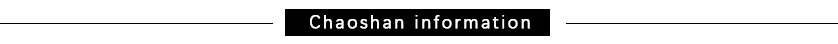
▼
 |
|
王富仁先生最后的岁月,是在汕头大学;其生命的终结,在北京望京花园寓所。他的思想高度伫立于民国,在东西方思潮交织最为激烈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。他的一生,以他的方式,始终与王国维、蔡元培、鲁迅等站在一起……
先生在学界,情怀在家国,人在书斋,如入江湖之险!先生是可以在任何时期,但见不平,拍案而起的。他的骨头和脊梁,如鲁迅般坚硬。他是新中国知识分子中坚信自己的学问,以之立言,并将之悍卫生命尊严的人。他绝不苟且,处处以独立的人格面世的勇气和学识,令他的存在,成为学界潜在的典范。他置生死于度外的风度,我们并不陌生。他的人生,诚如烈酒,诚如甘霖,诚如炉中的炭火。他的坚强是惊人的。他早就是王国维和老舍了。他以这样一种方式谢幕,没有什么不光荣,一如他向来独立的选择。
先生和别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,他一直都是在写自己,而别人大多是在写他者。王富仁先生从不抱怨,而别人更多是在抱怨。这就是区别。当大家都努力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的时候,王富仁先生旁若无人地站出来,自说自话,自己嘲笑自己,并不说及他人。他的所有作品中,只有一个主人公,这个人就是王富仁,自己。即便他说胡适,写鲁迅、评巴金、论曹禺,他言说的依然是自己。他把他者当成了另一个自己,而已。
多年前,我和先生在北京隋园畅饮,主题当然是烈酒与龙虾,无关悲剧。早前,我请他在民族宫的“潮江春”,吃过龙虾刺身,此后,每到北京的第一件事,就是要与王富仁先生喝酒,请他吃潮州菜……
隋园人很多,那天,我们来迟了,找不到座,好多人在门外的小树林里等座。先生说到别的小餐馆,随便涮涮羊肉算了。我有些动摇,却绝不气馁。既然是潮州人开的潮州菜馆,几句潮州话不就搞掂了么?也趁机让先生体会一下潮州大佬的本色。我说服了店主,在小树林里摆上了他儿子做作业的书桌,权当餐桌,又从卧室搬来沙发,沙发太矮,添了两个枕头。想必先生从未坐过如此舒服的餐椅。等餐的客人们纷纷要求如法炮制,个子矮小肚腩却大的店主,用潮汕话大声吼道:“开玩笑!北师大教授,胶己人!”……
王富仁先生目睹这个过程,有些不安,他笑问:“怎么办到的?”我说:“用你的牌子,说将来他儿子考北师大中文系,问你找后门。”先生认真地问:“他儿子多大?”
“小学一年级!”
先生笑了:“还有12年,何况,我哪有后门可走?这他都信?”
“信。潮汕人一生都在铺路,走到哪,铺到哪,自己走不上,给子孙走。”
王富仁先生说:“我很敬佩潮汕人!他们总能心想事成,锲而不舍地做事,老天总是为他们开路,我很想知道潮汕人何以如此。我的学生中潮汕人不多,朋友中你算一个,方便的话,很想去潮汕看看,究竟是个什么地方?”
我借机邀请先生到潮汕走走。1994年,我邀请王富仁与陈骏涛先生来到潮汕一行。
我想,2003年王富仁先生终于落户潮汕,成为汕头大学终身教授,与隋园之夜和1994年的潮汕之行,是有关联的。
先生晚年移居潮汕,在他声名正隆之时离开京城,令许多人匪夷所思。正如当年他从山东到西北到北京一样,毅然决然。在全无征兆的情况下,他已安居汕头。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他赴任汕头大学的消息的。他从北京移居我的家乡潮汕,我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
先生正如夸父。他又是一位过分明白,不时自嘲,戏谑自身功名的行者,他自觉地去履行学者的责任。他亦焦渴,却不饮河,他亦走大泽。夸父是,未至,死于此;先生是,已至大泽,且知将死于此。他不是焦渴而死,而是到此而去。他明知这是所有人的悲剧,他自己也难以忤逆,但他宁愿在精神上悖反而归。他在终点上起始,用自己的手,掘开了一个新的结束。所以,当我接到他的死讯的时候,我马上明白,先生想象的那一刻,终于到来。而这一刻,在一星期前的一次通话中,我已得到了他明快而欣然的预告。
先生在电话那头,劝我不必去北京探视他。他朗朗地说:“我这就要回去了!”我们谈话的前提地点,是潮汕,这话通常指的是“在潮汕再见”的意思。而其文学修辞或常识修辞,都可理解为他在暗示一种永诀!只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没有把问题想得严重,以为他真的很快会好起来。
先生最后的时光在北京。可是,噩耗传来时,我却听一个与他很亲近的同事告诉说:“几天前,还在汕头大学见到先生,还一起说了话!”在那一刻,我没有惊骇。我相信先生的灵魂就在那里。就在汕大遛狗的林荫道上。只是不知道,汕大的人们,会不会在那儿为先生留下一点痕迹?哪怕是种下一棵以他命名的树。
和先生一起喝酒,是最快乐的事,我可以直视他的内心,那种透明,那种不羁,那种痛快的陈说。先生把一个让人污浊的世界,泡在酒里来看,看出了它的美丽和纯真,看到了自然的长成,率真的血性,其惬意快意难以言状。先生每回到南方来,在广州,在海南,在潮汕,我总是到野地找寻喝酒的地方,和先生畅饮。
那年先生来广州,在繁华的广州天河北,到处是豪华的食肆,我只想寻一处雅静的大排档。我很想请先生吃潮州菜。先生总是说他不过就是山东农民、西北土包子。我说:我更是,海南岛黎母山原始森林的山里阿哥,一个知青而已。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,我荣升您的学生,很是受宠若惊。他连忙打断我的话,笑说:“还是称兄道弟舒服!”他不忘顺带抬举我几句,反倒弄得我不好意思。就这样,有一搭无一搭地走进一家潮州菜馆。这是一家颇有经营创意的菜馆,店主是个潮州文青,只要花138元,可享受一份主菜:一小碗鸡鲍鱼翅。同时备有138种潮汕小菜,酸甜苦辣,生的熟的,半生半熟所谓“含”出来的蚬、蛤等各种海贝,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,任取,随便吃。完了还可再点一份炒菜或炒饭等等。亦可自带酒水,不限,不收开瓶费。店主有些共产主义信徒的味道。八九十年代的人还真有些纯真,像还没被改革开放污染过的白云珠水,清亮清亮的。这种状况,令王富仁先生眼界大开,也很愕然,居然还有明知可能亏本而为的潮汕老板!后来,我又带北方朋友去这家菜馆,在原地址怎么也寻不到,一问方知,菜馆只开了几个月,早已关门大吉,去开夜总会了。再后来,听说这位潮州文青,成了酒行老大,酒厂就在白云山下的棚屋里,那里专门生产法国南部的百年轩尼诗。有次碰见他,他告诉我,别喝洋酒,还是喝回三块钱四两的北京二锅头为好。我说与先生,先生很是吃惊。
我一直想陪先生去海边吃野生的河豚,潮汕人叫“青乖鱼”,一般无毒,但非常美味。潮汕有习惯,餐桌上可以“乖鱼”宴客,但不可以邀人或劝人吃食,吃食与否,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,宾客自便。此习俗更添“乖鱼”的神秘。我之想陪先生去见识一下“乖鱼”的美味,并非劝先生吃食,而是觉得先生在潮汕,不吃一回乖鱼包括生腌,似乎很难真正从精神或情感上贴近潮汕人。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,盖因为先生在潮汕的这些年,似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,至少,感觉他渐渐喝不了太多的酒。一起吃饭,我再不主动请酒,渐觉出他的心重。
先生为什么在晚年,离开他熟悉的北京?说实话,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,最需要王富仁先生。有些事,我不愿意多想,我从未为此问过王富仁先生,先生的决定,自有道理。有些道理,是我辈永远都无法洞悉与理解的。所以,在我得到先生的死讯时,很是吃惊,但知道先生是以那样的方式谢幕,我反而释然。
先生已经远行。读他的遗作,读先生为拙著所作的序,读先生的旧信,追忆与先生在一起的日子……先生就在那里,在无数可能记忆的地方……
2015年1月,郭小东文学馆开馆,北京上海等地来了许多专家学者。王富仁先生专程来广州,由学生陪着。我给他定机票,他说:人那么多,别管我,我坐高铁来。那次,我感觉先生十分虚弱,我突然发现,先生戴上了帽子。原来十分精壮的先生,走路竟有些气喘,看得出身体大不如前。他住了一夜,第二天上午开完会,他就俏悄走了。我很内疚,多谢那位陪他的学生。他在电话里朗朗笑说,你忙,我好着呢!
2016年,又是一月份,《铜钵盂》首发及研讨会在汕头举行。这次,他一个人来,我陪他用餐,说了很多话。有好几年没一起喝酒了,可是,先生已经滴酒不沾了。他突然问我:“听说你们那个学科没了?”我一下子懵了,他直视着我。我回过神来,方明白他所指为何?他深深叹气:“很可惜啊!简直是犯混!太无知了!”他很严肃。我不知从何说起为好。
2003年,我所在学校文学院的二级学科“中国当代文学”学科要上硕士点,全省有几个竞争对象,名额只有一个。先生所在学科是其中最强大的。我与主管申报的林伦伦副校长及几位导师,专程去了汕大,拜访王富仁先生,盼先生支持,实际就是让出一条路。先生私下对我说:“放心,早就应该了!”那一年,我们申报成功。我明白其中不能言说的隐曲。十年来,我们这个学科有很大发展,其“中国知青文学”,在2012年,成了广东省特色重点学科。2015年,学校为了谋求更大发展,说是根据什么政策,可以把有成绩有硕士点的二级学科,置换成一级学科,以获取更多的教学与学术权益,从二级直接晋升一级,而规避了诸多条件。
这种所谓“置换”,其实是一种学术兑水,把一个经过几十年积累的“中国当代文学”学科,变成毫无基础毫无中坚的“传媒学”。究出何说?这是先生的原话。
“你不坚持?这不是你的学术风格啊!”先生戳到我的痛点,我无言以对。先生很少有这样具体尖锐的质问。
我想过坚持,但是,你抵抗不了集体的利益,那些虚无得高尚的说辞,和无数滥竽充数的期待。何况,当真有一个崇高的信仰或事业,值得渺小的个人去坚守吗?我自问。
先生隐忍的批评,令我无地自容。我很无奈地说:“当年真不该去截了先生的……”
“那倒不然!记得吗?去年我给你写的几个字!”在条形餐桌边,我与先生相对而坐,先生的目光在别处。
他说起题词,我自然记得,题词镌刻在格木上。先生题道:“岭南文化之子,知青文学之父——王富仁题赠郭小东教授 二O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”。
若不是珍重先生题词,我不敢公开,令人汗颜。先生说:“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,是文学的良知,知青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无法绕开的重大课题,中国高校只有你们学校有‘中国知青文学’学科,如此草率就放弃了。”先生叹气!又说:“你的知青文学创作和评论都做得好,更不能放弃!”
我一时语塞。先生的文学大义和坚执,无人不知,我相形见绌,只好敬先生一杯茅台。此刻先生忌酒,我乃自饮。周遭人声鼎沸,杯觥交错。我悄悄扶先生下楼,嘱司机小心慢开。先生有些蹒跚,想必他心中明白,彼此颇为伤感,此乃一诀。
又过了几个月,我去牛田洋,见雾气里先生住的高楼,遂邀先生一起去南澳住一晚,先生说很想去,但有些不便,怕添麻烦……我有些惶惑,未及深思。
斯人已逝。
以先生之傲骨,追未来之理想。
曾经的风华,茂林修竹一般的形意与形胜,在污浊的世事中,暂栖于诗与酒,在曲尺形柜之内外,神意游走。这一次,便是若干年后潮汕的启应。潮汕人,应感悼王富仁先生。把对韩愈的纪念,相与先生。
|
你是本文的第736位读者
来 源: 摘自“汕头日报”2017、10、22
作 者: 郭小东
|
| |
| |
| |
▼

特别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《图·文》来源于国际互联网,仅供参考,不代表本站立场!
本站尊重知识产权,版权归原创所有,本站资讯除非注明原创,否则均为转载或出自网络整理,如发现内容涉及言论、版权问题时,烦请与我们联系,微信号:863274087,我们会及时做删除处理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