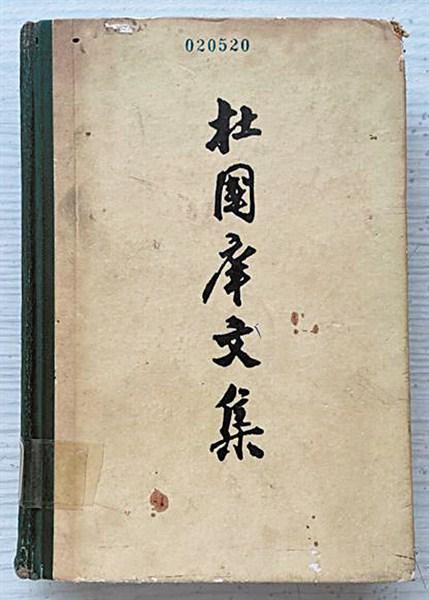▼
| 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前期的100多年间,潮州地方社会经历了一个急剧动荡、由”乱”入”治”的历史过程,原有的社会秩序和地方权利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在这一过程中,围绕着”海盗”问题所开展的种种活动,对后来的潮州社会和人们关于”潮州文化”的理解,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。 一般说来,明代后期东南沿海所谓”倭寇”和”海盗”问题的产生,直接与明王朝厉行”海禁”的政策有关。明朝立国之初,一反宋元时期政府容许、鼓励海上贸易的做法,除有限度的由王朝直接控制的朝贡贸易外,规定”寸板不许下海,寸货不许入番”,以严刑峻法禁止私人的海上贸易活动。然而,东南沿海的粤、闽、浙诸声百姓至迟从汉唐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海上贸易,从中获利颇丰。这种地方文化传统与明王朝法令之间的矛盾,蕴含了由此而引发地方动乱的可能。 实际上,有明一代,东南沿海民间非法的海上贸易活动始终未曾停止。就潮州而言,正统年间已有滨海之民”私下海通爪哇”(《明英宗实录》卷一一三)的记载;成化二十年(1484)又报告说,”有通番巨舟三十七艘泊广东潮州府界”(《明宪宗实录》卷二五九)。至于到海外以后,利用朝贡机会,”冒滥名色,假为通事”(茅元仪《武备志》卷二一六),再回来”专贸中国之货,以擅外番自利”(《明史》卷三二三)者,也是举不胜举。当时的广东地方官员和市舶太监出于稳定地方社会、增加军需供应和贪图贿赂等各种考虑,对这种状况实际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,到正德年间还好似”听其私舶往来交易”(《明武宗实录》卷一九四)。 嘉靖以后,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1521年嘉靖皇帝即位之初,重申了明初有关海禁的规定,嘉靖二年至嘉靖八年(1523-1529)一度停止广州市舶;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二十八年间(1547-1549),提督浙闽海防军务的朱纨进剿宁波附近”下海通番”者聚集的双屿港,上蔬揭发浙闽势家通倭谋利,又追击海上私商和葡萄牙人于福建诏安之走马溪,大获全胜。这一系列时间,正好发生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品货币关系空前发展,商人和地方势家力量增强,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利结构正在”转型”的关键时期,从而引发了长达百年的东南”海盗”之患。正如嘉靖四十二年(1563)福建巡抚谭纶所奏:”今岂惟外夷,即本处鱼虾之利,与广东贩米之商,漳州白糖诸货,皆一切禁罢,则有无和何所于通,衣食何所从出,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?”(《谭襄敏公奏议》卷二)嘉靖后期开始,能够自由来往于海上,并操有实际海上利益的,绝大多数是违法犯禁的武装吉他–海盗,其中又以漳潮海盗牵连最广,影响最深。 在双屿港被明朝军队剿毁以后,位于闽粤交界海面的南澳岛,逐渐成为新的非法武装贸易据点。南澳岛”旧番舶为患,洪武间奏徙,遂虚其地,粮因空悬”(嘉靖《潮州府志》卷一)。这个”幅员三百余里”,距大陆仅10余海里的岛屿,从明初开始就没有任何官方机构管理,也没有编入里甲、交纳赋税的”编户齐民”,从而成为海上走私贸易的理想场所。据《东里志》卷一载:”(南澳岛)惟深澳内宽外险,有腊屿、青屿环抱于外,仅一门可入,而中可容千艘。番舶、海蔻之舟,多泊于此,以肆抢掠。······长沙尾,西跨南洋,近于莱芜澳,为船艘往来门户,海蔻亦常泊焉。”日本商人亦来此贸易,”定期于四月终至。五月终去,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。其交易乃搭棚于地,铺板而陈所置货物,甚为清雅。刀枪之类,悉在舟中”(郑若曾《筹海图编》卷三)。 以南澳为根据地或在这里有较多活动的,包括了嘉靖年间漳潮地区所有的重要海盗集团,其主要人物有许栋、许朝光、、曾一本、谢策、洪迪珍、林国显、徐碧溪、林道乾、杨老、魏朝义等。作为有时拥有数万之众的海上武装集团,他们活动的范围已经源源不限于海上走私贸易,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性质。例如,许超光除在南澳修宫室、建敌楼、筑城寨外,也”分遣其党,据牛田、鮀浦诸海口,商贾往来,给票抽份,分曰买水。朝光居大舶中,击断自姿,或严兵设卫,出入城市,忘其为盗也”(乾隆《潮州府志》卷三八)。又如,林道乾先在南澳活动,后被明朝招抚,仍继续招兵买马。他设营寨于广澳,泊战船百余艘于靖海港,其党众则分别安置于澄海县各处地方,魏朝义据鮀浦,诸良宝据南洋寨,莫应敷据东湖寨,遥相呼应,一度成为地方官府的心腹大患。这些海上武装集团的活动范围遍及闽粤两声沿海,也到达日本、吕宋、交趾、苏门答腊、柬埔寨、暹罗等地。林道乾、林等先后在加里曼丹、吕宋等地建立过殖民据点。也有记载说张链和吴平兵败以后到了三佛齐和安南。 在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,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礼法制度受大了严重的挑战,”民”与”盗”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。正如王世贞在其《岭南弭盗案》中素讲的:”其始也,海蔻焉而已,山蔻焉而已,今而郊之民蔻也,郭之民蔻也,自节帅而有司,一身之外皆蔻也。”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(1545-1547)任潮州知府的郭春震,在编修《潮州府志》时特别指出了当时潮州海患的原因:”一曰窝藏。谓滨海势要之家,为其渊薮,事觉则多方蔽护,以计脱免。一曰接济。谓黠民窥其乡道,载鱼米互相贸易,以瞻彼日用。一曰通番。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,挟私货,百十为群,往来东西洋,携诸番奇货,一不靖,肆抢掠。” 隆庆至万历初年,潮州沿海的治安情况稍有好转。隆庆二年(1568),明王朝接受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,开放海禁,准贩东西二洋。万历三年(1575)起,明朝在南澳设副总兵,以水兵3000人专守此地,从而限制了海盗集团的活动,然而,隆庆二年开海禁,实行的是”引票制”,文引之数有限,又限定贩洋的货物与范围,对海上贸易仍然是很大的妨碍。而万历中期以后,南澳也出现了海防废弛的情况,战船裁减,士兵参与走私。结果,万历末年亦寇亦商的海上武装走私活动再度活跃。当时在潮州沿海活动的海盗集团首领包括袁进、李忠、杨六、周三、钟斌、六香、李芝奇等人,其活动一直延续至明代末年。当然,与嘉靖年间相比,这一时期海盗集团的规模、社会影响和活动范围,都显得小一些。 崇祯十三年(1640),原为海盗、后受抚于明朝的郑芝龙就任南澳总兵,4年后升任福建都督,总兵一职由其部将陈豹接任。陈豹任此职几达20年之久。明清鼎革之际,尽管郑芝龙于顺治三年(1646)降清,但陈豹管治下的南澳仍然奉晚明正朔,南澳成为郑成功反清复明活动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。郑成功多次从这里出发进攻大陆各地。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,郑氏武装集团一直是东南海上最实力的控制者,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,基本上独揽了通洋之利,南澳也成为其海上贸易的重要基地。 康熙元年(1662),由于明郑集团内部矛盾,陈豹降清。同年,清政府在潮州沿海实行大规模的”迁海”政策,南澳岛和大陆沿海数10里居民全部内迁,民不聊生,哀鸿遍野。 当时潮州沿海唯一驻守”界外”,继续进行海上贸易的海海盗,是在达濠建寨固守的邱辉。乾隆《潮州府志》称:”邱辉受郑经伪札,开府于达濠埠,置渔盐之利。”他还一直与明郑政权统治下的台湾进行贸易,对潮州沿海乡镇也时有骚扰。康熙八年(1669),潮州各地”复界”时,特别规定达濠仍为”界外”。不过,邱辉的所作所为已是百余年来潮州沿海海盗活动的余绪。康熙十九年(1680),清军平达濠,邱辉下海遁走。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清政府统一台湾,同年开海禁。潮州沿海为时100多年的以海盗活动为中心的大规模海上走私贸易活动,终于告一段落。 明清之际潮州的海盗活动的社会意义,并不仅仅局限于与海上贸易有关的内容。与海盗和反海盗的一系列活动相联系,这一时期潮州府的地方政区被重新划分,聚落形态出现了某些军事化的趋势,以宗族组织和民间神祭祀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也重新整合,户籍和赋税制度亦有重大的变化,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解释有了新的内容。这些都为有关”海盗”问题研究的深入,留下了广阔的空间。 |
|
▼
特别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《图·文》来源于国际互联网,仅供参考,不代表本站立场!
本站尊重知识产权,版权归原创所有,本站资讯除非注明原创,否则均为转载或出自网络整理,如发现内容涉及言论、版权问题时,烦请与我们联系,微信号:863274087,我们会及时做删除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