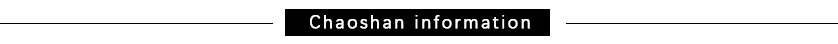
▼
 |
|
解读一个人很不容易,起码需要时日。
知道他的名字在1957年,那时我在念高中。是年,潮州大锣鼓《抛网捕鱼》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联欢节上大出风头(洋专家说“闻到鱼腥味”),捧回了象征祖国荣誉的金质奖章,司鼓便是他,甭说有多酷!在举国上下认同“苏联的今天便是我们的明天”的岁月,他一时成了家喻户晓的凯旋英雄,四处作报告,听他讲苏联“老大哥”的种种见闻,还有那个“娜塔莎”……那是崇尚英雄主义、理想的年代,觉得与他的距离是那样遥不可及!想不到两三年后便相识,再往后,还成了风雨共济的同事。
1960年我在文联,他在文化局艺术科,同栋楼办公。一场強台风令我们奔赴韩江堤上抗洪。云低、水急,风抽、雨打,日色渐晚,我等四条汉子奋战了一天,顿觉饥寒交迫,这才醒悟到四人支队没后勤,成了没娘的孩子!怎生是好?“天无绝人之路;我去想办法!”林自告奋勇,话落人便没入往市区方向的雨幕中……个多钟头过去,一声“来啰!”他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,“幸福生活在眼前!”变戏法似地把铁桶盖子揭开:嚯,是温热喷香的炒饭!原来是从曲艺团讨来戏饭。初出茅庐的我,自惭百无一用。
事隔七八年,我们又一次风雨共济,不过,这回面对的可是“史无前例”!
我们一起蹲“牛棚”。当“牛”前,他在曲艺团当曲艺队队长,我则在潮剧团编导组混饭。“牛棚”日夜有人监管,亮着“长明灯”(大功率灯泡剧团仓库有的是),有一个就悬在我头上(我在上铺)。“牛”们彼此不能说话,哪怕任何交流暗示的小动作(我就吃过告密者的亏)。白天除干脏重活便是“背靠背”写交代材料,随时有戴红袖章的监管人员来“提堂”,点到谁,谁便被押走,此刻不知下刻的命运,大有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之感。下午四五点是形同“放风”的时刻,我们扛着大扫把等洁具,煞似手执长矛的堂吉珂德,杀进街对面原潮剧团团址浴厕搞卫生。浴室厕所一溜儿,只用薄杉木板隔开,本就隔“墙”不隔耳,加上作业时有冲刷声掩护,正是交换“情报”的好时机!
一日紧急集合,气氛异常。“斗、批、改”领导小组“抓阶级斗争新动向”,要“革命群众擦亮眼睛”,“把丧失立场向阶级敌人通风报信的人揪出来”。我登时惊出一身冷汗!用戏文来说,叫“事因如此如此”:蒙革命群众开恩,我得以率先出“栏”,名曰“解放”,闻市属四个表演艺术团体集中办班日子行将结束,人马连“牛”将分成两拨,一到牛田洋,一到东径劳改场。我于是瞅准“牛”们“放风”的时机,佯装“方便”,隔着板墙将此信息透露给林运喜 。这下子祸闯大了,我才享有几天跳“忠字舞”的政治待遇哪!度日如年中,又瞅准“作案“时机,忐忑不安心照不宣与林擦身而过,一闪进厕所关上板门,便听到林在外面发话:“无(说)诶!”一句“无诶!”让我即时捡回一颗掉进冰窖的心!后来查出是话剧团某演员向某泄的密。某演员属“红五类”,经一番“斗私批修”,无事。漏网的我,则侥幸逃过一劫!
“9·13”前,我们从“五·七”干校“毕业”,一同分配到工农兵文化服务站(文化馆、工人文化宫的替身),成了“同个战壕的战友”,他当文体班文艺组组长,我是大兵(辅导创作、编小报)。此间有件说小不小的怪事。一日,站长宣布抽调几个人脱产挖防空洞,鄙人荣列其中,说是“老黄在干校搞过基建,有经验。”天知道这是没影的事!“唔(不)对!待我探听一下。”林知我有难,主动去“侦破”,证实是头人有意给我小鞋穿,宽慰我:“勿惊!”幸得他幕后斡旋,使我免多受一场劳役之苦……换作今时,主动搭救别人的人有几多?!
不久我便调往文工团编导组,后又去路线教育工作队,回城进了文化馆,林是副馆长。时长日久,我们之间免不了也有不愉快的事,不过,也仅仅是那么一回。那天轮到我值班。林去外面办事返馆,见当天的报纸仍散在办公桌上没上报夹,突然发火,追问是谁值的班。我这个人有时很犟,猜他可能是在外边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,便既不答话也不动作。在场同事也觉得他反常。事隔没几天,市府办分配给我一套新居室,“日月换新天”,但面积只有30多平方,只好加搭个小阁楼,故需购置一把小竹梯。计划经济年代,物资匮乏,少花钱多办事是国人持家之道,吾每月人工仅四张多“大团结”,想到他认识在竹器厂当头的业余文宣队员,便不顾前嫌拜托他。他一口应承。于是有了这样的镜头:他吹着唿哨,一手抓擦拭得锃亮的双铃“永久”单车车把、一手攥着挂在肩头的小竹梯,一个漂亮的刹车,立在办公楼门外阶沿前……还有一件事。我曾在萧殷老师府上当过食客,知道萧老对汕头沙茶酱印象甚佳。可那时市面稍为好一点的沙茶酱属国营商店柜台里的“陈列品”,我只好又求助于他。他不但给解决了,还趁出差代我送到省城梅花村……
1987年,在举办一次大型群众文艺活动后,我们出行西安、太原和北京。到西安机场出口处,忽见他出奇招:把随身携带的一只尼龙袜子套到手掌上高扬。我等正莫名其妙,接风的人已来到面前——亏他想得出这接站的暗号……
他归入“发挥余热”行列后,活力不减,成天骑着28吋单车到处转,继续他的“大锣鼓”,出CD专辑,还整理一批锣鼓乐,誊印后曾送我。活动量大体力消耗自然大,白天也得“加油”。有次到小摊吃汤粉,自知牙门不好,便先打招呼:“同志姐,来个银粿条勿猪肚。”同志姐即时还他白眼:“都什么年头了,一块钱还想配猪肚?!”……他不时到单位来。每当大楼梯道传来他那“专利”潮音散板“伟大的党啊,是慈爱的母亲……”大伙便知是他驾到。有一回他忿忿然告诉我,在报上读到演《人到中年》出了名的潘虹说今后要努力于悲剧角色的创造,甚反感——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,他不容社会主义文艺与悲剧沾上边。
1995年他患上顽疾,人一下子像风干了似的。从无法多出门到出不了门,对天生闲不住的他来说,实在够残酷。他依然关心天下事,订阅多种报刊,包括《足球报》(外间谁相信长着罗圈腿的他居然是个足球拥趸)。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字词、典故或别的什么“奇难杂症”,他便打电话给我,末了,不忘叮嘱:“单位的事,慢慢来,乜事都想开!”他理解我受命于危难之际,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,专业抛荒,心力交瘁。这句友善好心话,令我感念到如今!
我担心他在单位不景的日子里倒下。眼看他一年一年挺过来了,忽报撒手归去……40年前兮40年后,或许是上天安排,让我在临近退休之年主持处理他的身后事。他生前是中国音协会员、汕头音协名誉主席,潮汕各地和广东民间音乐曲艺团,战士、海政、总政歌舞团,海外潮人聚居地,都有师从过他的弟子。在潮汕,一提潮州大锣鼓,人们便会想起他——一代鼓王林运喜!说来惭愧,鄙人不谙平仄、对仗,当日为满足逝者后人之求,竟置路数脸面于不顾,破天荒为告别式撰了一副大挽联:“满腔真诚化潮韵/一双鼓槌写人生”。市作协主席陈焕展在纪念文章中提到,称是对其“艺术生涯的准确概括”。但我总觉得还没说到最是处。
我寻思:林运喜出身贫贱,日里沿街叫卖,夜间拜师学艺,苦熬苦学终成出类拔萃的民间艺人,这就决定了他的平民属性(立场)。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。他一生没生育。他的人脉是修来的。他热心助人,事无巨细,可理解为侠行。他的不出卖别人是以道德良心为底线的。这一切,并非每个被称作人的人或事业有成者都具有。而他生性乐观,在生活里便常常体现为老顽童的行状,很容易被误读成“俗”。
林运喜这个人,平民底色,人味十足,广结善缘,乐天不老——其实,这才是我最想要说的话。
|
你是本文的第807位读者
来 源: 摘自“汕头日报”2017、7、30
作 者: 黄廷杰
|
| |
| |
| |
▼

特别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《图·文》来源于国际互联网,仅供参考,不代表本站立场!
本站尊重知识产权,版权归原创所有,本站资讯除非注明原创,否则均为转载或出自网络整理,如发现内容涉及言论、版权问题时,烦请与我们联系,微信号:863274087,我们会及时做删除处理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