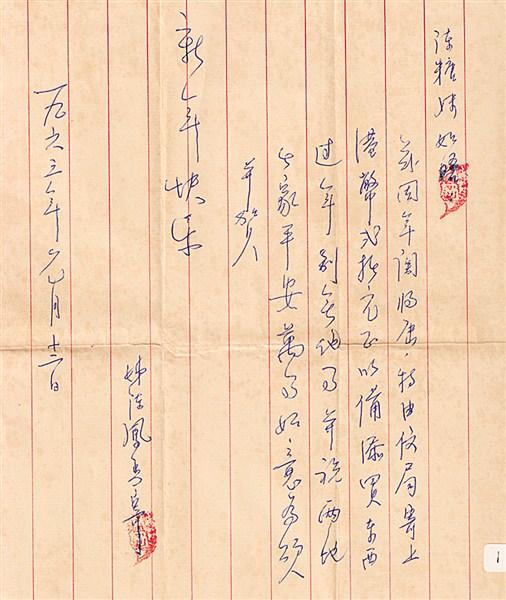▼
| 有一次,一个朋友问我:“若全世界让你选一个城市定居,你选哪里?”我说:“京都。”她又问:“中国呢?”我说:“潮汕。”说不出为什么,也不知具体原因,就那样轻易答了潮汕。那是离北方极远的一个城市,但有说不清的魔力——像爱一个人没头绪没理由,以为不爱她但夜夜全是她,每个缝隙里全是她。 我第一次来潮汕,但不觉得隔阂,只觉得来过很多次了,以至于有些恍惚,仿佛是在这里住了很久的人,亦像是宋朝失落的亲人,因战乱逃到南国,隐姓埋名到今朝。那风物竟熟悉到可以热泪盈眶,居然是心最深处的旧相识。 我和家和认识约略三年。她的名字真好听,家和,我常默念这个名字。看她发的潮汕老宅图片,花朵、猫、狗、老人、老树、坛坛罐罐……每每就有了买张机票飞去的冲动。徽州、婺源、江南小镇每年都去,只是一直没去最想去的潮汕,因为觉得它太合自己的口味——那样浓情的一个地方,我相信会一见如故。 家和隔一段时间便寄来一些我喜欢的旧物——潮汕的点心模子、旧的竹花碗、用过的腌菜坛子。她从来只用文字与我交流,我当她是我在潮汕的他乡知己。见过一张她拍的荷塘,飞鸟、荷花、老房子、旧宅前的猫。她说:小禅,你来了,我们在这里喝老茶。 这句话我记了三年,慢慢生了根。丁酉年正月,想去潮汕过元宵,订了机票就走了。我告诉家和要来潮汕了,“她”忽然开了口,是男声。家和居然是男人,我自以为他是女人好多年。 网上订了载阳客栈,客栈在巷子里,一座老宅改成的。影壁上画了孤杉,条案上摆着橘子。空气中潮湿的味道,还有说不清的味道。 已是临近黄昏,家和出现在客栈。中年男子,戴黑边眼镜,灰色禁欲系衬衣。我们在小巷中游荡。潮汕三轮车真多啊,铺天盖地,刹那间恍如在越南街头,老树遍地。街头到处是卖潮州三宝的,“三宝”是老药桔、老香橼、黄皮豉。老香橼又称老香黄和佛手果,是佛手经中药秘泡而成,乌黑发亮的色泽,浓厚的佛手香,据说舒肝气,治胃病。买了一罐回来,每次喝都想起潮汕来。 街上有好看的小庙,庙里有木雕、古画、嵌瓷,尤以嵌瓷最美,五颜六色的瓷器嵌在屋廊、房檐上,又艳丽,又脱俗,妙极。我总是在那繁复的嵌瓷屋廊上注目很久。南方的细腻不仅体现在老香黄上,还体现在木雕、砖雕、嵌瓷上。 路边有卖卤鹅肉的人,小摊,支着一盏昏黄的灯。家和说这家小摊从他小时候就有,有30年了。买了一盒卤鹅肉,边走边吃,又看到路边的“八尺娘酒”,觉得这个名字迷人。坐在路边讨了喝,甜且辣。 小茶盘红红的,里面是喜字。八尺娘酒放在喜字上,我端起放下喝了三杯。胸中有了潮汕意味,便坐下听家和与他们说潮汕话。 潮汕话与粤语和客家话又不同,酒家的电视正放潮剧,有一种无法诉说的哀怨之气,是《四郎探母》,仿佛南宋过来的遗民永远忘不了的中原。南方的剧种无论梨园戏、潮剧、南音、粤剧都有挥之不去的软湿哀伤,也说不清楚哪里让人动容,听着心里就会浮起一坨哀伤来,糅合着南方特有气息,更叫人欲罢不能。 天黑下来,旧宅门前挂着红灯笼,尤喜潮汕人家宅子前挂着的竹编灯笼。有的上面写着自己姓氏,有的涂成红色,在夜色中像狐狸眼睛,妖媚极了。 一转到了牌坊街,牌坊是新的,少了些味道,但因一排又一排,又有了气势。坐在百年老店胡荣泉吃小吃,简直不知要吃些什么好。鼠壳粿、春饼、笋粿、鸭母捻、蚝烙、牛肉丸、沙茶粿……粿这个字在潮汕闪着异样的光芒,没哪个地区几乎把小食全叫粿。 那做粿的模子也好看,木制,生动的图案,因为用久了有了柔润的包浆。我收藏了几个,用来做了茶托。 在潮汕的一周我吃了各种各样的粿,它们生动地活跃在我的胃里、DNA里,至今忘不了。这个名字有着特别的光泽,它只属于潮汕。 这里的风物古风荡荡,仿佛觉得自己来过很多次,其实是第一次。我是潮汕的故人,相互认出彼此,刹那归去来辞。 |
|
▼
特别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《图·文》来源于国际互联网,仅供参考,不代表本站立场!
本站尊重知识产权,版权归原创所有,本站资讯除非注明原创,否则均为转载或出自网络整理,如发现内容涉及言论、版权问题时,烦请与我们联系,微信号:863274087,我们会及时做删除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