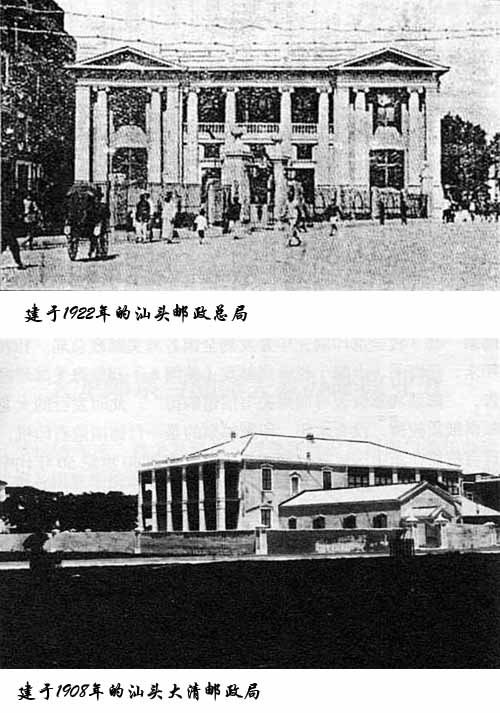▼
| 按一般通行的说法,韩愈在潮州刺史任上,曾着实干了四件事:一、祭鳄驱鳄;二、释放奴婢;三、奖励农桑;四、延师兴学。描述这些政绩的文章甚多,这里不赘。我思考的问题是:什么才是韩愈谪潮最大的亮点?上面所说的这四件事,相信一般较有人民性的官吏,也都会这样做,但作为“唐宋八大家之首”的韩愈,他是“高度理性和超人文采集于一身者”(丛维熙语),只有他,才能与高僧大颠作那种机锋警敏的儒僧对答和探索玄妙深奥的禅理。大颠乃南派禅宗大师,早年于海潮岩(西岩)出家,拜曹溪派系的惠照为师,在南宗禅创始人惠能的第二代传人希迁禅师处获得曹溪真传。与这样一位南派禅宗大师对话并留衣赠诗:“吏部文章日月光,平生忠义着南荒;肯因一转山僧话,换却从来铁心肠。”,这才是韩愈谪潮最大的亮点。 据史载,韩愈与大颠大约见了三次面。第一次是韩愈祀神海上,顺道上灵山拜谒大颠禅师;第二次是大颠应邀到潮郡,韩愈接待他住大稳庵(即叩齿庵),大约住了十多天才返回灵山寺;最后一次是韩愈调任袁州刺史前夕,到灵山与大颠告别,赠衣留念。在这个过程中,韩愈曾给大颠写了二封信。 通过这些交往,韩愈称赞大颠“颇聪明,识道理”、“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,不为事物侵乱”,但“与之语,不尽解”。那么,韩愈与大颠到底谈了些什么呢? 孟简(唐大臣,元和中,官至太子宾客,分司东都)在《大颠别传》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述,兹取大意转录如下: 颠:今子之貌,郁郁然似有不怿者,何也? 愈:因贬而祸患不测,冀万一于速归。 颠:子之死生祸福,其命岂不悬诸天乎,汝姑自修而任命可也。 愈:佛家无死生,无欲无念,无喜无忧,然愈岂能妄取空语,安于天命乎?佛者,夷狄之一法耳,自后汉流入中国,汉宋陈魏,事佛弥谨而莫不夭且乱也。 颠:佛者天下之器也,其言则幽明性命之理,其教则舍恶而趋善,去伪而存真。 愈:佛者不谈先王之法,而妄倡乎轮回生死之说,身不践仁义忠信之行,而造乎报应轮回祸福之故,使其徒不耕而食,不蚕而衣,践先王之道。 颠:心地无非,佛之常乐。如孔子言,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;佛之与人子言,必依于孝;与人臣言,必依于忠。此众人所共守之言也。 愈:儒家之道,孝悌忠信,是以不耕不蚕而不为素餐也。 孟简笔下的这段对话几近杜撰,类乎创作,他怎么可能如此详尽地了解韩愈与大颠对话的内容呢? 因此,对其真实性大可不必去追究它。但这段对话却另有其研究的价值,这就是:为什么孟简要让大颠说出儒家的话来呢? 这个问题很有趣,要回答是既易又难。易者,可以说这是孟简时刻站在老友韩愈的立场上,刻意贬佛,让佛门大师向儒学投降;难者,则可能与当时的佛儒交融的大气候有关,也许孟简是有意无意地在“创作”中融合进了“当代意识”。 那个时代,正是唐德宗倡导儒、道、释三教调和的时代,孟简让大颠接受某些儒学,当是合乎道理的。有论家亦已指出,“难得的是大颠对一些儒家之道亦有所解”。如果这样解释得通的话,那么,韩愈会不会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一些禅理呢?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蔡涵墨在《禅宗 中有关韩愈的新资料》一文中介绍,由福建泉州招庆寺静、筠二禅德编撰于南唐保大二年(952)的《祖堂集》,是现存的初期禅宗史书的最古本,其第五卷载有石头希迁弟子的传记,开卷便有大颠和韩愈交往的记载。 |
|
▼
特别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《图·文》来源于国际互联网,仅供参考,不代表本站立场!
本站尊重知识产权,版权归原创所有,本站资讯除非注明原创,否则均为转载或出自网络整理,如发现内容涉及言论、版权问题时,烦请与我们联系,微信号:863274087,我们会及时做删除处理。